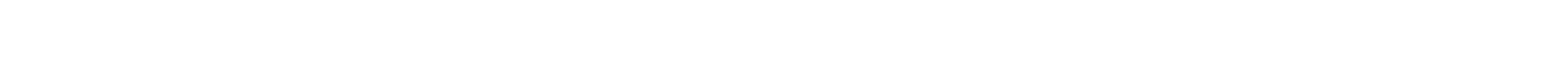方显廷与《天津地毯工业》 | “文献里的天津”之天津地毯故事
来源:城市记忆故事 2025年03月13日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叫方显廷,他可以说是天津地毯工业研究的开拓者,其《天津地毯工业》一书,对早期天津地毯工业的状况进行了详细调查。

方显廷,浙江宁波人,著名的经济学家。1929年到1948年,方显廷在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后改名为经济研究所)工作了19年,曾任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主任兼文学院经济系经济史教授,将南开经济所创建成为中国第一流的经济研究中心和研究生培训基地。1929年到1937年,方显廷连续在天津工作了8年。直到卢沟桥事变发生后,1937年7月下旬,方显廷受张伯苓校长的派遣离开天津辗转赴长沙准备国立第一临时大学开学事宜。自此,方显廷离开了天津,并再也没有回来。
方显廷出生于1903年9月6日。根据宁波乡音,“廷”和“定”两字发音相同。因此,“方显廷”名字中的“廷”指的是“固定不动”。小时候,方显廷家中没有同龄玩伴,也不敢同街上打架斗殴的顽童待在一起,因此他的父母认为他总是“定”在家中。方显廷生在珠宝首饰商人家,但没有出生在家庭财富的全盛时期。在1906年,家中遭遇大火,家中房屋被焚烧。不久,家中二哥行为放荡,沉湎嫖娼,盗走珠宝店中所有的现金和珠宝,使得家中沦为赤贫。受这种打击的影响,方父在方显廷7岁的时候就离开人世了。

小时候,方显廷在一位秀才开办的私塾小学校中开始读书认字。在方显廷大约10岁左右,转学到了宁波斐迪小学开始学习英文。他在学业上居第一名。这也为方显廷赴美留学提供了可能性。到了1915年,方显廷从斐迪小学毕业,继续在一所职业学校学习一年后,因为家境贫寒难以继续求学。1917年,在方显廷14岁的时候,经过亲戚介绍,他独自乘坐轮船来到上海,成为杨树浦厚生纱厂的学徒,遇到他的伯乐——穆湘玥(藕初)。在20世纪,穆湘玥被誉为“中国棉纱大王”,是厚生纱厂的经理,也是方显廷的恩师。1920年,穆湘玥资助他在南洋公学(现交通大学)附属中学读书,继而资助他于1921年秋天赴美深造,直到1923年夏天穆湘玥因为财政损失,才中断了对方显廷每月80美元的汇款。

何廉是方显廷在耶鲁大学的同学和同宿舍室友,也是方显廷心中的兄长,更是南开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的创始人。1928年北伐成功之后,中国进入到国家重建的新阶段,并且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工农业的发展。当时学术讨论围绕着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开始工业化的问题。何廉以天津地区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对中国工业化程度与影响进行探讨,并选择地毯工业为调查对象。地毯工业虽然是手工业,但是地毯产品几乎全部供出口,对现代化城市的工业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何廉在这方面还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因此,何廉向担任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推荐了方显廷,让方显廷担任研究委员会的研究主任兼文学院经济系的经济史教授。因为方显廷对于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工业结构很有研究,而中国的工业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情况与当时的英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因此,在1928年,何廉劝说刚刚回国的方显廷放弃在上海的高官厚禄,与他一起开创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任教经济史,担任研究所的调查研究主任,并准备一份关于天津地毯工业的调查报告。

方显廷初到天津时,仅仅25岁。被分派到百树村19号客房的一间居室,与何廉、理学院陈礼共同居住在这所客房内,对门正对着蒋延黻教授的家。1929年7月4日,方显廷和发妻王静英结婚后,便迁入南开教工居住区百树村的一所平房。房子里家具什物一应俱全,一切由学校供应。

《天津地毯工业》作为中国工业系列的第一篇专论文章,方显廷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以致于他在和妻子结婚的第二天一大早,就起床直奔木斋图书馆的办公室,去敲击打字机的键盘,以便完成关于天津地毯工业的调查报告。虽然这一调查研究此前已经由何廉和一位助手开展。但是因为收集的情况不够充分,方显廷不得不重新开始这一工作。方显廷经过对地毯工业的概括了解和对手工编织地毯的作坊的实地调研。这份报告最终在方显廷结婚的当月完成草稿,并由方显廷进行文稿的编排和版式打样、校对,由直隶印字馆印刷出版。方显廷也指导了如何将出版后的这篇文章分发到国内、外第一流的图书馆,目前美国和英国的许多图书馆都可以找到这份调查报告。

《天津地毯工业》是根据1929年的实地调查,以社会经济方面为研究主体,研究经费部分来自于太平洋国际学会拨付的款项和北平社会调查所的津贴。由天津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出版。英文版在1929年10月出版,中文版在1930年8月出版,目前《天津地毯工业》已经收入《方显廷文集》第2卷。在这份调查报告完成后,方显廷的恩师——穆湘玥为它作序。1930年7月(民国十九年七月),穆湘玥在序言中提到“天津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从事实地研究已经很多年了,已经取到了很好的成绩。现在刊印《天津地毯工业》,作为工业丛刊第一种。这个举动是增加生产的必要步骤”。 那么作为方显廷到达天津之后的进行的第一项调查报告,《天津地毯工业》在调查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困境,又是如何解决的?这份调查报告又具体讲了什么,他与地毯工业之间又发什么了什么故事?

《天津地毯工业》这篇调查报告是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写成的,但是在研究方法上有所改进,逐步抛弃了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做法。何廉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他们在调研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最为明显的问题是调查对象很少合作,不愿交谈而且没有知识。最开始在研究地毯工业时,是向调查对象分发征询意见表,然而这种在美国极为普遍的做法在中国却完全失败了。因为当时被调查的人员拒绝填写这些意见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到天津地毯工业的各个厂家,进行个别交谈。然而,这种做法也不可行。因为方显廷他们不熟悉地毯工业的的“行话”,并且是外来人员,往往把受访者都吓跑了。更为让调查人员感到苦恼的是调查对象丝毫没有数字概念。如果问他们有多少资本,他们就回答“没多少”。如果问他们挣多少钱,他们就回答“很少”。如果又重复问“有多少?”,答案还是“很少”。问工人“你们每天干几小时活?”他们便会答“时间很长”。继续提问“有多长”,答案还是“很长”。迫于这种情形,方显廷他们尝试查看工厂的记录,以便获得更确定的答案。然而他们因为缺少情报来源,而束手无策。最后只能设法从工业部门寻找一个人来为他们工作,再从地毯行业寻找两位调查员。这三个人没受过现代教育,他们和要调查对象一样缺乏统计数字的概念,并且对工作也不感兴趣,但是对这项工作所支付的薪水很感兴趣。何廉曾在回忆录中这样写到“他们对我想干点什么和为什么要这么干都感到莫名其妙,实际上他们干脆认为我是在干蠢事”,他也曾自嘲“在中国采用调查的方法进行实际经济研究,还不如偷偷打听呢”。在花了大量的时间培养他们的业务能力,并多次向他们强调准确记录数据的重要性后,天津地毯工业的调查报告终于取得了一些进展。
《天津地毯工业》的英文版于1929年10月,由天津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出版。方显廷赴美留学达到长达7年之久。当他回国后,中文演讲和中文写作都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他往往用英文写出手稿,由他的助手译成中文,再由方显廷检查核对内容无误后,最后则是由何廉的学生——李锐检验定稿。李锐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学基础,并能写得一手好字。他实际上是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的中文秘书,研究所所有的文献手稿以及对外通信都要经过他的检验。因此,《天津地毯工业》先是英文出版,然后才是中文出版。

我们在了解了《天津地毯工业》报告调查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后,让我们通过《天津地毯工业》这篇调查报告,来了解一下20世纪20年代天津地毯工业的发展现状。
1904年,中国地毯在圣路易国际展览会获得了第一奖。国内外对地毯的需求量日益增加。自此,国内的地毯工厂相继设立,地毯工业日益发达。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近东地毯来源闭塞,中国地毯成为了西方各国的热门选择。而天津作为羊毛出口的中心点,蒙古、青海、甘肃等地所产羊毛用铁路、船或者车运到天津,使得天津在1929年成为中国地毯织造的中心点,并将中国所产地毯的百分之九十都销往海外。出口销售的主要国家有美国、日本、英国。运输地毯需要缴纳统税、出口税和进口税。1923年开始,中国城市运输地毯到天津租界需要缴纳统税。虽然在天津运输地毯需要交以上三种税,但是自1912年天津都能维持其出口第一之地位(除1921年因商业清淡外),这也奠定了天津是中国第一地毯出口商埠的地位。直至1926年国民革命北伐战争发生,交通梗塞,运费变高,各地毯工厂品质下降,西方各国的消费者不再争先购买中国地毯。地毯工业才出现衰落的情形。
天津地毯业的工业组织是由商人雇主制过渡到工厂制。截止到1929年,天津地毯工业制造所有303家。按照当时国民政府工商部暂行工厂法规定,任用30人以上的制造厂所,才可以被叫做合法的工厂。因此,天津的地毯工厂一共有105所,其他的198家地毯制造所都是地毯作坊。在这105家地毯工厂中,大多数都工人使用木制长方形的织机工作,用转运机器当做原动力的工厂是很少见的。这些工厂制造者的组织大部分是商人雇主制,和作坊基本没有区别。商人雇主制下的地毯制造者承做出口商号的定货,制造者自己只需要准备工作场所、少数织机、刀剪和织毯所用的经纬棉线等各类必要的工具,并为工人与学徒提供住所和膳食,而商号供给地毯所用的毛线。这类商人雇主制的地毯工厂资本较少,仅仅足够支付工人的工资和房租这类的流动开支。

地毯工厂中工人数量是根据营业范围之大小而定的。地毯工厂及作坊中的工人很多是雇于营业活动的时候,一旦营业停滞,就立即解雇。1925年—1929年,全工业中织机增加,因此工人的入厂时间大部分都在这一时间段内。天津地毯工厂及作坊的工人,有细工、粗工和学徒三类。粗工人数是最少的,细工工人数最多。细工工人在大工厂中,大部分人是从事织造工作,少部分人是织匠的工头和学徒的老师。工人大多大部分人信仰佛教,文化水平较低。来自河北省的工人居多,大半的工人是由朋友介绍而来,很多工人的年龄普遍在17岁到29岁。然而地毯工人结婚的年龄较迟。在当时的中国,结婚年龄多为16到18岁,但是工人结婚的年龄可以提升到20岁。细工与粗工都是按劳分配,多数是在每月阴历的月初或月半领取工资。每月平均工资是在6元—9元之间,最低不少于4元,最高不超过11元。饭钱和房钱不算在工资之内,需要额外支付。饭钱通常是每月6元,房钱每月大约5角。因此,细粗两工每月实际收入,大约在11元5角至14元之间。而织匠的工头和学徒的老师则每月可以获得固定的工资。此外,学徒没有工资,只有膳宿费。学习期满之后,学徒可以平均可以得到一笔18—24元的礼金。虽然学徒没有工资,但是将学徒的训练费、生活费和浪用材料费一并计算,学徒的花费实际是超过雇用细工需要的费用。
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经济研究领域普遍缺乏实地调查,对统计数据的重视程度也相对较低。然而,《天津地毯工业》调查报告自1928年筹划至1929年10月出版,却提供了大量精确的统计数据。在当时的中国,这样的成就无疑是一项显著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