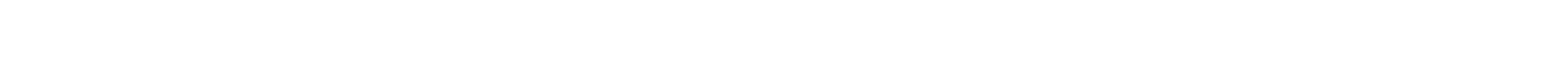想念“老头刘”
来源: 《今晚报》 2025年5月9日 17版
何 平
翻阅泽华师晚年的赠书,扉页题字的落款多为“老头刘”,让我想起一段往事。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南开大学读博士,彼时,刘刚、冬君伉俪正携幼子刘涵宇读刘泽华先生的硕士研究生。我们砥砺学问或闲聊时,说到先生,径称“老头”如何如何。谁知听者有意,一次我们一起去先生府上述学,小涵宇冷不丁告了一状,说:“刘爷爷,他们在背后叫您老头呢!”童言无忌,却令我们无比尴尬,那时先生才50多岁,正值盛年。先生拊掌大笑:“哈哈,我就是老头呀!”算是解了围。
大学里学生对师辈的称谓,尤其是私下称谓,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读书时,对有民国学术经历的师辈,称“先生”而不称“老师”。对上世纪50年代之后高校毕业的师辈,多称“老师”而鲜称“先生”,亦有直呼为“老×(姓氏)”者。我想,“先生”之称或许表达了对老一代师长学术造诣的仰慕,颇有望之俨然的意思。而“老师”“老×”之称就有些“亲民”了,一者他们离我们年龄最近,代沟较少,二者他们就学治学时期,须借助对学术的虔诚和百倍的努力,才能由“老师”抵达“先生”。
据我所知,学生们对泽华师的称谓最为全乎——“刘先生”“刘老师”“老刘”“老头”。称“先生”,尊师重道也;称“老头”,可敬可亲也。
泽华师是严肃的,面对原则问题,面对披着学术外衣的各种巧佞,他眼里揉不得沙子,总会奋起辩难,不避矢石。面对后学,先生是宽容的,帐下弟子多个性峥嵘之人,多惊人可怪之论,然而每有一得之见,先生从来不吝誉辞。师生间的驳难争论即便面红耳赤,先生亦习以为常。
先生设教,一直致力于破除“师教唯一”的信息茧房,他鼓励学生在关涉政治思想史的学科领域信马由缰,举凡政治学、哲学、心理学、宗教学、神话学、人类学、社会学乃至体育学等,刘门弟子均有涉猎,有些人甚至到了沉浸旁门,“久借不归”的地步,如宗德生兄即由政治思想史而入精神分析学,终入哲学之门,另辟蹊径,先生不仅不以为异,反而赞赏有加。
正因为如此,“王权主义反思学派”才能凸显其特有的谨严与丰赡,思想史是全部人类历史的花果与结晶,只有动员充沛的学养与智慧才能揭示其词语、范畴背后的逻辑与风景。先生构建了中国政治思想史开放性的学术体系,在先生的教诲、感召与激励之下,弟子、后学和同道以其各自的学养和创造力共襄盛事。
先生作为一种“思想的存在”和“学术的存在”已无需赘言,其思想之犀利、著述之宏富、影响之深远,丰碑自在。这里只说先生作为“老头刘”的一件小事:1999年上半年某日,我请先生、师母家宴,先生对我做的红烧肉大加夸赞,说:“你们南方人食不厌精,太会享受,所以老被北方民族征服。”我立即“反击”:“明朝、民国可都是北伐成功。”相视一笑。这时先生神秘兮兮地说:“我会你们南方美食的一个绝活,你未必会。”我问何种绝活,先生笑而不答。数日后,师母电话通知我去取“绝活”,原来是先生手工自制的酒酿,清香扑鼻。此物是南京秦淮小吃“赤豆酒酿元宵”中的必备之物,作为饮品单吃亦可,冷藏后的酒酿,其味清冽隽永,更是盛夏消暑佳品。先生馈赠,尤称我心!但是总不能以口腹细事屡扰先生吧,我多次请先生“授人以渔”,先生总是一笑置之,秘不示人。在津多年,我们一家一直享用着先生的自制酒酿。久居金陵,每当我品尝酒酿,或听到街巷里售卖酒酿的梆子声,总会想起先生那种神乎其技的孩童般的得意,泪眼矇眬……
想念先生,想念他的思想机锋,他截断众流的勇决与果敢,也想念“老头”作为父辈的慈祥和不避烟火气的人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