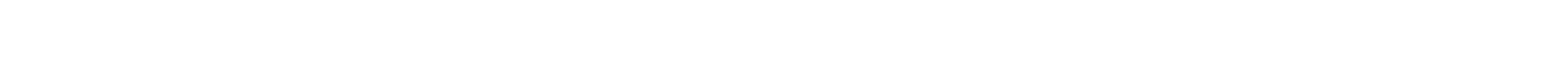世变沧桑中的进退与扎挣——戊戌变法到晚清新政间的严修心影
来源:《南开大学报》2025年3月28日(第1482期)第3版

陈 鑫
今年是严修先生诞辰165周年。近日,《严修日记(1898—1910)》整理完成,日记中这10年多的时光既是严修个人从40到50岁的年华,也是戊戌变法到晚清新政的历史时期。作为珍贵的一手资料,日记中记录了严修亲历的重大事件与日常点滴,反映了他的教育救国事业和心路历程。这一时期,严修从贵州学政卸任,戊戌变法中受保守派打压而回乡归隐。此后经历庚子之变的动荡,因国难危急再度出山,积极投身于天津、直隶乃至全国的教育改革事业,为推动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付出艰辛努力。然而,复杂的政治环境使他终因得罪摄政王、对政局失望而再次退隐。
日记体量庞大、内容丰富,如何提纲挈领地理解严修10年心史,本文采取“诗史互证”的方式,将严修的自述诗与日记结合,勾勒他在“世变沧桑”中的进退与挣扎。1909年,按中国传统是严修五十初度,他写下《五十述怀》组诗共4首,彼时他正处于学部左侍郎任上,诗的内容正是十年经历的记录,与日记相呼应。
世变之忧与家国担当
世变沧桑又几经,十年风景话新亭。鼎湖影断朝霞阙,(两宫大丧尚未奉安)剑阁声残雨夜铃。(距辛丑回銮未满十年)大地江山几破碎,中兴将相遍凋零。河清人寿嗟何及,但祝神狮睡早醒。
《五十述怀》第一首诗开篇,严修回顾了十年间国家所经历的沧桑巨变。自己五十寿辰之际难言喜悦,感慨的只有对国运的忧思。“新亭”典出两晋之际,当时南渡诸人因山河破碎在新亭对泣,而王导则呼吁共赴国难。严修用此也流露出不甘沉沦、渴望奋起救国之志。
国难首先是庚子之变与辛丑条约,京津沦陷、帝后出奔。严修亲身经历惨状。天津在战乱中沦为人间炼狱。他先是因家塾教授新学,险遭义和团抄家;后又在八国联军陷城烧杀劫掠之际,与亲友困守城中。在危难中,严修收留了亲友男女老幼300多人到家中,还尽力为众人备办饭食、寻觅医药,但仍有不少人不幸罹难,包括自己的多位亲人。这些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国家和人民的苦难,下定决心广开民智、教育救国。另一重大变故是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去世。作为政坛高层,严修亲历这一过程,在日记中有详细记载。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一朝天子一朝臣,人事更替意味着政局动荡。而此时“中兴将相遍凋零”,朝中已没有能够力挽狂澜的政治人物,怎能不让人更加忧虑。
诗的最后先用“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古典,再用“东方睡狮”喻中国的今典,表达的是个体生命有限,与其为“小我”祝寿,不如祝福中国这个“大我”。所谓“神狮”不是指皇帝也不是清王朝,而是中华民族,相比于一家一姓的生死存亡,严修更关注的是现代意义的国家、民族,他办教育之目的就是要培养不同于旧王朝旧臣民的新国民,建设新国家。正如张伯苓多年之后的评价:“彼(严先生)之国家观念,我人今日尚未能追及。”
人事代谢与时代反思
最堪思慕最堪伤,师最恩深友最良。(李文忠师、徐东海师、张丰润师、贵坞樵师、陈君奉周、陶君仲铭、王君寅皆均歾于近十年)筑室至今惭木赐,(四师之丧,余适家居,均未会葬)铭碑何日托中郎,(余欲撰亡友诸人事略,乞当代君子铭诔,以不达于辞,至今未果)秋阳江汉风千古,华屋山丘泪几行。逝者全归复何恨,剩余百感对茫茫。
第二首诗字面上表达了严修对十年间亡故师友的深切怀念,实则也是对时代的反思。诗中列举了李鸿章、徐桐、张佩纶、贵恒等老师和陈璋、陶喆甡、王春瀛三位挚友。
李鸿章与严修的师生关系,是从他作为直隶总督亲临天津问津书院考课学子开始,此后多有指点。当时张佩纶是书院山长,他对严修治学更是给予过重要指导。徐桐、贵恒是严修的座师,即科举考试中的主考官,有知遇之恩。严修感念师恩,但在大变革时代,他与老师们的思想并非完全一致,甚至在有的方面差异巨大。比如,严修尊重徐桐是理学名家,但老师极为厌恶维新。严修因为推动变革科举,在戊戌变法前夕被徐桐逐出师门,这也是他第一次归隐最重要的原因。严修尊师重道,但坚持己见。
诗中严修提到的三位友人,是新思想、新事业的先驱。陈璋对科学技术充满兴趣,还有着朴素的男女平等观念。严修在18岁时与他结识,深受其影响。陶喆甡重视经世致用之学,积极参与维新活动。王春瀛在天津兴办新学之初,是严修最为重要的帮手之一。从日记中看,庚子之变后,严修与王春瀛、林墨青、张伯苓等终日讨论兴办学校,几无一日不过从。
古人说:“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复何恨”,人生怎样才能算无恨呢?国势如此,上述师友的结局又该如何评价?最惨的是徐桐,义和团起,他盲目地认为“中国自此强矣”,结果八国联军入城,他只得自杀,死后还因主战被追责论罪。李鸿章年近八旬奉命北上谈判,油尽灯枯而亡。张佩纶闻联军攻陷大沽,咳血升许,带病参与谈判,后病逝。陈璋、陶喆甡死于战乱病疫,王春瀛壮志未酬身先去。他们的死可以算是“无恨”吗?严修此时尚身在局中,面对茫茫的前途,怎能不百感交集。
渔竿初志与治病仁心
两度瀛山采药归,渔竿初志竟乖违。(余癸巳旧句云“有约环瀛纵游后,万花深处一渔竿”,乃今自倍其言)不惭高位腾官谤,可有微长适事机?推毂徒贻知己累,滥竽敢恃赏音稀?百年分半匆匆去,差向人前忏昨非。
严修的一生经历了出仕、归隐、再出仕、再归隐的历程。早在30多岁任翰林编修时,因为与旧官场格格不入,就曾表达在环游世界后回家隐居的“初志”。可是,当他真的出国考察后,反倒开启了出山从政的人生新阶段。
严修将自己1902年、1904年两次赴日本考察,比作“瀛山采药”,因为他认为中国要摆脱困境,必须在文明交流中取长补短。回国后,他放弃了归隐的初衷,应袁世凯之请出山主持,将直隶教育事业办成全国典范。国家成立学部,他又担任侍郎,参与主持全国教育事业的顶层设计,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学部提出“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也正是念念不忘以教育治私、弱、虚等“中国之大病”。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严修深知政局的复杂,他担心自己在家乡的办学事业会因从政而受到影响,无法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尽管如此,他还是全身心投入学部工作中,是最勤政的堂官。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政坛上遭遇的挫折越来越多,对自己的选择也越发怀疑。日记内容与诗中所表达的矛盾心情相互印证,展现了严修在初志与现实之间的艰难抉择和内心的痛苦挣扎。
冒死谏言与无奈归隐
恶风卷海浪横流,秦越相携共一舟。何屑升沉谈宠辱,莫缘同异定恩仇。随波每怵趋庭训,(先君有句云“落红无力恨随波”,盖喻言也。)补漏弥怀忝祖忧。(先本生王考歾时,余年十三,病中召余榻前,训之曰:“若兄诚笃,吾无忧,若佻薄,可忧也。古句云‘马行栈道收缰晚,船到江心补漏迟’,小子慎之。”今三十八年矣,言犹在耳,每一追诵,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五夜扪心呼负负,君亲恩重几时酬。
严修之所以再次心生退意,是看到当时政坛上的混乱。光绪、慈禧死后,摄政王载沣掌权,打压异己,将袁世凯排挤回家。但出于对国家的责任,在无人敢言的情况下,严修冒死上奏折进谏,呼吁摄政王与各方同舟共济。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严修引用父亲、祖父的训诫作为掩饰,还特意加以注释说自己“佻薄”“可忧”。对严修了解不深的人往往觉得,他只是温良恭俭让的恂恂儒者,这并不错。但每逢遇到大是大非的紧要关头,严修又总是勇于直言,绝不明哲保身。当年因上奏折建议改革科举被老师逐出师门,是如此;此时冒死得罪摄政王,也是如此;此后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又进京诤谏,更是如此。
诗的最后,严修写到自己忧心忡忡、彻夜难眠,是写实。日记中可见不少记录,如“夜半醒,有所感触,辗转不成寐,不能退,不能遂,如之何?如之何?”“四钟梦醒,枕上思学务要件……”严修关心的不是自己的“升沉”“宠辱”,而是国家的得失,这也与第一首中的“但祝神狮睡早醒”相呼应。实际上,《五十述怀》四首诗内容虽然各有侧重,但主题是高度统一的。所谓“不能退,不能遂”,正像范仲淹所说“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是严修十年中的心境写照。对家国天下的使命担当与混乱政局中难有作为的不堪现状,造成了严修在出仕与归隐之间的纠结。
严修的正义之举并没有得到朝廷的认可,反而得罪了摄政王,被以莫名其妙的借口罚俸半年。当时的清廷与现代国家相差太远,在参加赴东陵为慈禧、光绪送葬时,严修听到大太监呵斥“官任何大,终是奴才”,深感厌恶,彻底失望。
最终,严修不再作无意义的挣扎,第二次归隐。但他并没有放弃救国之心,而是在家乡着手社会改良,继续锐意办学,推动市政、工商、卫生、慈善、赈灾等公共事业。正如1908年,他创办的南开学校首届学生毕业时,严修在训词中讲道:“勿志为达官贵人,而志为爱国志士。”他说这不仅是对学子们的勉励,也是学校创办的宗旨。实际上,这句话正可视为严修本人的精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