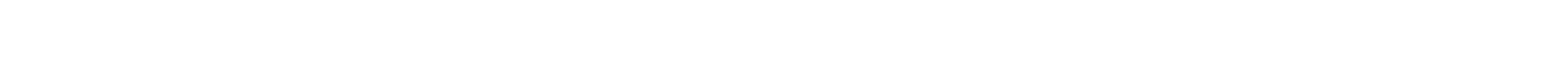文科谜思·矿科兴废·造境津郊——南开大学早期校史漫思三题
来源:《南开大学报》2025年3月28日(第1482期)第3版
王 昊
文科谜思
历史上号称“文以治国”的南开,实则并不太重视人文学科的建设,这已在校史上有所记载。可是,在大学的奠基时代,文科建设似乎还颇为有声有色,其中一个原因是梁启超曾经的短暂“加盟”。当时,欧游归来的梁启超寓居津门,开始了晚年的研究生涯,南开抓住这一机会,欲借重其来建设文科。
1921年9月,梁启超移砚南开,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影响波及京津。在此期间,严修、张伯苓等人与梁启超往还频频,很希望其能助南开一臂之力。1921年年末,梁启超在和张君劢、蒋百里、舒新成等友朋通信中,多次提及与张伯苓筹划南开文科的事宜,梁透露了南开欲聘请张君劢出任文科主任,请蒋百里、张东荪、林宰平“各任一门”,并计划邀请梁漱溟到南开任教的信息。用梁启超自己的话说,“若将文科全部交我,我当负责任,彼欢欣鼓舞已极”,“吾六人者任此,必可以使此科光焰万丈”。
晚年的梁启超,虎老雄心在,深感当时国内从事文史研究之人的匮乏,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登高一呼,率先振发,能够达到号召天下,集合同道共同担负起振衰起敝的责任。他甚至设想“南开文科办三年后,令全国学校文史两门教授皆仰本科供给,其所益不已多耶?我辈努力兴味正浓也”。同时,梁启超还认为如果以其师生、师友为南开文科班底开展教学和研究,并将“此科旁通于理、商两科,则根底于全校”,这有望成为未来中国学术界的“关中、河内”!当时参与讨论的张东荪、蒋百里、舒新城等人更是摩拳擦掌,希望梁氏能尽快与学校细订纲领,规划科目进行组织,从速落实此事。
可令人迷惑的是,无论是从1921年起深受鼓舞并“每见必询消息”的张伯苓,还是频繁鱼雁传书讨论南开事且认为“绝无问题”的梁启超,对于南开文科的制度建设给人以有始无终的感觉。而到了1923年初,如何建设南开文科的事情似乎已经不大被提及了,转而演变成看似“一切学课与南开保相当之联络关系”,实则私人讲学意义大于机构建制的“东方文化研究院”之议了。
如果仔细探寻历史细节,我们就能发现在讨论南开文科建设时,梁氏所倚仗的蒋百里、张君劢、舒新成、张东荪等人,尤其是蒋百里和张君劢,深具德国教育的背景,在办学理念上其实与南开相去甚远。蒋百里曾设想,希望梁启超与南开确定一个办法,将其“中国历史研究法”归为讲座之一,同时再约梁漱溟、张君劢、张东荪,加上他自己分别担任讲座教授,“每座讲演之期为四个月,文书口头研究之期为六个月,因每座专为内部学生不收外人”。
对南开而言,“梁启超版”的文科之所以虎头蛇尾,令人抱憾,实是历史的偶然,于己有憾,对梁氏师友则无所谓遗憾可言。一方面,1922年间的梁启超并没有“一心一意”地按照他与师友信中所谈的那样逐一落实制度建设;另一方面的原因,恐怕还是缘于张伯苓校长,因为在他看来文科生“文章做到像张季鸾在《大公报》写的社论那样水平,就到了顶峰”,而所以请梁氏主讲“中国历史研究法”,因为“张校长对近代史感兴趣”,一旦梁启超以“‘诗圣杜甫’为题的讲演(见《曹禺传》)我估计张校长的兴趣就不大了”。
1922年和1923年之交,“梁启超版”的南开文科一变而为“东方文化研究院”后,南开人还颇多期望,“甚盼此番计议早见施行,裨东方文化得大放异彩于环球也”。实际上,若从梁启超《为创设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的启事来看,他认为“现在学校制度种种缺点,欲培养多数青年共成兹业,其讲习指导之方法及机关之组织,皆当特别”,这种机构应该“采用半学校半书院的组织。精神方面,力求人格的互发;智识方面,专重方法之指导”。计划中的文化学院设有专门招收中学毕业生的“本班”,专门招收大学及大专毕业生的“研究班”,以及招收高师学生的“补习班”,不能来院学习者的“函授班”。除教学外,文化学院还拟从事整理古籍、将旧籍和新著翻译成欧文,编写文史教科书、出版同人著述、巡回讲课等工作。不难发现,这所拟议中的学院,其私人讲学的性质已跃然纸上。
所以说,文化学院的无疾而终,固然是困于经费、人员,更主要的则是归因于梁氏个人难以“八表经营”而造成的“眼高手低”。文化学院最终逃不出缺乏明确的规划和落实而造成流产的结局。但更有研究者综合时代、国内环境和个人因素等背景考虑,认为北洋政府除了“相关政策上支持和鼓励外,并无办学经费上的资助”;梁启超虽登高呼吁,但景从者寥寥;而且梁氏精力过于分散,根本无暇时时顾及“文化学院的创办以及办学经费的筹措”。论者最后指出私立南开文化学院的“无疾而终”是“与国学教育在近代中国私立大学中的时代境遇有关”,因为“私立大学在专业设置方面显得更为务实,常会选择一些实用性较强且易于就业的专业”,这决定了文化学院的专业设置或称国学教育在私立南开办学过程中的堪忧处境。
矿科兴废
20世纪20年代中期,私立南开大学虽然巩固了基础,但在学科布局上还是处于不断地调整和适应阶段,与相对稳定发展的理科和商科相比,文科与矿科在发展上略有曲折,不过与前似昙花一现的“东方文化研究院”和后来的“采集中精力政策以振兴”的文科相比较,曾经被广泛看好、有望成为“国内大学办有矿科之嚆矢”的南开矿科竟也没有与学校“共进退”,在存在了五年之后终被取消,着实地令人感到意外。
是否因为矿科存在时间不长,以致校史上的记载过于简要、后人的回忆模糊不清?校史上称其自1921年秋招生开办起,只设一班不分系,聘任薛桂轮为地质学教授兼矿科主任,并相继聘任李子明、孙昌克、王德滋、臧毅清、曹诚克、沈天民等教师,到1926年因捐资人李组绅停止捐款而停办。这几年间的教师选聘、课程和实习的设计、出版刊物及学生情况均无过多的笔墨涉及,这个具有独立董事会的学科在南开校史上竟好似一个“鸡肋”般的存在。其可见之记述比之于有始无终的东方文化研究院的记载似乎更为零散,也缺乏系统的整理,诸多历史信息杳渺无迹,矿科的面貌也不甚清晰,不由得让人心生疑窦!
其实,矿科虽在1926年停止办理,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私立南开时期的“大学一览”“同学录”中都曾保留了对矿科创办人及董事会成员的记录。
实际上,矿科自成立后,在校内外均有很好的口碑,张伯苓就曾对商科的学生们说:“我们学校里,现有文、理、商、矿四科。文、理、商先立,矿科是后添的。但论起精神,矿科最好。它的原因是什么?据我想矿科每个暑假有练习,同学得在一块儿玩耍或讨论,所以其乐融融,感情甚好。矿学会的组织,虽然也有教授帮助他们,确是个自动的组织,成绩最好”,“南开大学教育目的,简单地说,是在研究学问和练习做事。做事本就是应用学理。将平日所得来的公律、原则、经验应用出来到实事上去”。作为首任矿科主任的薛桂轮在后来的回忆里也曾记述:“我对矿科学生也只时时勉励他们专心钻研科学技术,不谈时事,不讲政治。还始终不放暑假,于四年学制内利用三个暑假,由我亲自率领他们到华北各地本国实业界自办的煤矿,实地练习测量、采矿选煤方法与调查地质工作。”在学的矿科学生也确如张伯苓和薛桂轮所说,立志在学习上“研究砥砺,以求进益”;在实习中跟随老师不辞劳苦,认真向学,每到一处矿山实习,“早上七点钟的时候,就背了仪器,带了水壶,走出十多里外的山里,或者下到三百尺深的矿中去测量”,“有时候就有身边带几个馒头及一些咸菜,坐在野地里或煤堆里一吃”。在师生共同追求进步的岁月里,大家都怀着一种奋发向上的、“富源自辟”的决心努力着,所以在大学初期的精神面貌上,南开矿科确乎异于其他三科。
按理说,以这样的发展态势,南开矿科当有更为理想的未来。但是,天有不测风云,1926年因时局变化加之煤矿经营不善,李组绅无法继续为南开助款,导致矿科停办。自1923起,李氏年度捐款已开始减半,1924年就基本停止拨款了。对照1926年6月出版的《天津南开大学一览》所载,李氏一共只捐出了现洋八点五万元,与预期尚有很大差距。捐资助学虽然可以看作是个人或团体的一种道德的积累和实践,但这里面还交织着捐资方与受益方在利益上的博弈和冲突,纯粹的道德是无法保障和支撑一项事业的。校长张伯苓曾说:“我为自己向人开口捐钱是无耻,为南开不肯向人开口捐钱是无勇。”从矿科兴废事件背后反映出来的,正是张伯苓平衡道德与利益关系的真情实景,也是他所一直倡导的化私为公的具体操作。他对于捐资方已经明确捐助给学校的款项,绝不含糊一分一厘,甚至不惜对簿公堂,梁启超曾评价其“此公办事权限分明”,绝非虚言!
造境津郊
大学之魂,当在学人风骨;大学之美,必属校园风物。
1931年秋,新生黄燕生怀着激动的心情和无限的美好向往,迈进了八里台南开大学的校门。由大中桥进入校园,他用一双好奇的眼睛仔细地打量着校园内的一草一木:
走上大道,一只圆形大钟就出现在你眼前……校园中心是一片十字形的湖塘……南面,湖塘尽头是理、工学院的教学大楼思源堂,右畔是文、商学院的教学大楼秀山堂……桃花丛中的女生宿舍芝琴楼距它只有咫尺。
思源堂西角的百树村里,是一幢幢小巧玲珑的教师宿舍,村中心是一块草坪网球场。只有男生宿舍,在远处大操场的一角上……在这段小小的征途中,也自有其独到之处,肃静的木斋图书馆,离他们住处不远……思源堂后,墙子河尽头,是一片景色迷人的芦苇湖……校园与市区间隔着长长的沿河马路。
这只是上世纪30年代初的大学景象,黄燕生眼中景色优雅的南开大学实际上并不大,校园景色一眼便可望穿,与同时期的或雄伟庄严,或典雅古朴,或中西合璧的其他大学校园相比,私立南开的大学景色并不显山露水,但“水”是校园的一大特色,“整个学校不仅被支河细流所环绕,就是校内也是小溪纵横交错,南北通达,具有水乡田园风光”。
其实,大学部初建,暂且依傍在中学部附近“栖身”只不过是权宜之计,早在1920年,南开人就开始为进一步拓展办学空间而频频谋划。本来计划在中学南面购地一百七十亩建设大学建筑,后因诸种原因改为“永租本埠城南八里台北公地两块共二百七十亩”,“南一百六十亩”,共计四百余亩作为大学拓展办学规模的基础。一所大学创设之初,当然需要“优秀的教师”;当然需要“完善的设备”;当然需要“充足的经费”;当然更要之者,不能缺少必要的可持续发展的空间,那就是“校园”和“大楼”!南开人在选定八里台作为大学校址的时候,这一带只不过是“带着绿荫与荷塘”的“荒凉一片”。20世纪初,八里台一带水网密布、芦草丛生,对大学选址而言,似乎并非是个理想的所在。
从地理空间和学校经济要素考虑,以天津城市近郊的八里台作为新校址,明显比原来计划在中学部附近购置校址更为划算。尽管这里似乎并不适合筑基造楼,但南开人就是在看似不可能的条件下,先是在天津城西南的地势较低的开洼地带———南开洼———建成了国内闻名的私立南开学校,继之在八里台这片水洼之地上建起了一所闻名国内外的大学。“但这次大学并未因迁到新址而更名。此时‘南开’这个名字已经取得了如此特殊而深远的意义,无法再为人们所遗忘。”
1922年这一年,校父严修对“新南开大学”的建设显然投注了更多的心力,他频繁地前往大学部与校长张伯苓、伉乃如、华午晴、喻传鉴、魏云庄等人晤谈,时常能“谈极久”。此外,他还不辞劳苦地不定期前往新校址察看。4月18日,严修约范源濂考察大学新址,那时尚无直接通达的陆路,严修等人从海光寺一带“下人力车易小船巡视后返至原处”。后来他在致函侄孙严仁曾时,语气中略带着激动,称“曾乘舟周览两次”。至1923年上半年,严修对大学新址的考察,对新建楼宇验看的次数明显增多。这年7月12日,当严修携孙辈们“先乘人力车至海光寺前换乘学校所备小船”前往八里台新校游览时,私立南开大学已粗具气象。极少在日记中展露心境的严修却一改文风,记述下当时他站在新建的秀山堂前时的那种感觉,那景致“四望青绿一色,极为美观”,使人神气为之一振,舟车辗转的疲劳感顿时消解殆尽!8月23日,严修更是约集城南诗社同仁泛舟八里台,同游15人分成两舟,吟诗诵唱,尽兴而归。“最是差强人意事,居然城市有山林”;“日尽诗未尽,归棹南关头。去年此地来,岁琯恰一周。今年会益盛,友声又广求”;“故乡风景君应记,略似西兴到绍兴”……那种兴奋之情真是溢于言表!直到多年后,南开学子在依依惜别学校的时候,亦对泛舟八里台的那种情致久久不能忘怀,“天津缺乏支河细流,而八里台的南开却是左右逢源,南通北达。很似乎江南的水邨”,“南开河的妙处在蜿蜒曲折”,“一湾有一湾的妙处”。这一湾一湾的水道,每处景致各有千秋,或秋水伊人,或夹岸老树参天,或檐影斜侵、叶光掩映,或豁然开朗、别有天日。观老少南开两代人的风物文字,虽是诗随境异,各有所宜,但同是处在那种舟行水面、绿荫弥望的环境里,真个是让人顿生行云之在太虚,流水之无滞相之感。
暮年的严修对于新校的建造为何投入如此多的心血,显然与其对大学的期望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今的南开大学,草木之盛虽逊当年,但自然之境依稀可辨,小溪依旧,莲池如故,依然是那条笔直幽雅的大中路,连缀起一座座黉庐讲舍、书阁楼台。站在八里台的大中桥头,追想校父严修当日的奔波劳苦之状,徇其心迹,不禁使人感会其内心的波澜。严修晚年对私立南开看似“若即若离”,实则始终在场。私意以为,校父晚年对“新南开大学”的迷恋,多次假地八里台邀集同好诗成吟咏,并非是“愁极本凭诗遣兴”,更似是“借题发挥”,意在借同道之口道出“为忆兰亭游,倘亦同兹兴”的自家怀抱。时人尝说,校父生性风雅,“栽花植竹,为其生涯”,当年亲手种植卉木于南开校园中,每到花期,“辄觞诸名流,吟咏为乐”。颇有审美意识和极高审美造诣的严修,对于大学的建造,显然是出于一种绝不应该只追求于自然对人工建筑的容纳,也不应一味追逐地理空间上的扩充,而应着意于将“大学之道”贯注于或自然物,或建造物之中,更应将一种人文之美融入对大学理念的理解。然而,这些臆测仅是后人的一点遐思而已!
当年的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秀山堂、思源堂、芝琴楼、百树村等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大中路两侧,缓缓流过的溪水、一湾一湾的池塘让人感到舒适。尽管建筑物不以数量取胜,但木斋图书馆、思源堂、秀山堂等几座标志性楼宇的廊柱、高墙、屋顶与敞亮的开窗均十分宏阔,把整座校园妆点得十分古典和秀丽,无不让人感受到学府的庄严和魅力。整座校园布局规整而有序,也不失浪漫的色彩。如果有人在南池边小憩,就会望到“科学馆(思源堂)倒影,或是秀山堂的斜影。你斜着头,于思于思地想你的什么问题都行,水影微微地波动的漪涟,可以唤出的你的思潮”。当夕阳西下时,若站在北极亭或西极亭四顾,那洒满校园的金色,想必更让人感到肃穆中的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