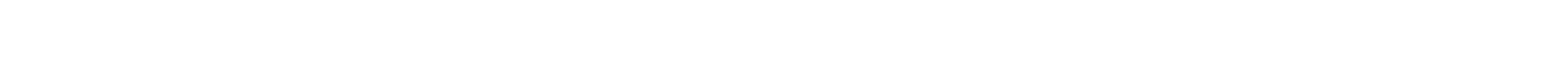勤敏追梦 终成大观——读刘岳兵《三集斋小集》有感
来源:《南开大学报》2025年11月7日(第1492期)第3版

刘运峰
1987年12月28日,19岁的刘岳兵在日记中写道:“一生想出三个集子:印集、诗集和文集。不知三者能否兼得,但我努力而为之。所以我自命为‘三集斋主’。”
“三十八年过去”,刘岳兵的这一愿望已经实现了。近日,江苏人民出版社集中推出了刘岳兵所著的《三集斋小集》,包括诗集《飞回古典鱼鸢堂吟草》,文集《追蠡精舍杂纂》,印集《二丘庵印存》以及集外集《南开日记钞》。名曰《三集斋小集》,实际一点也不小,而是分量厚重,内容丰富,洋洋大观。这套丛书的出版,使得刘岳兵成了名副其实的“三集斋主”。
刘岳兵是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的院长,他在日本近代儒学研究、日本近现代思想研究、近代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研究、南开日本史研究等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了《日本近代儒学研究》《中日近现代思想与儒学》《日本近现代思想史》《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等专著,发表了100多篇论文,主编了《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至竟终须合大群——南开日本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等大型图书,堪称国内日本研究的著名学者。
但是,学者本色是诗人。
刘岳兵虽不善言辞,但多情善感,这正是诗人的特质。
在正式出版《飞回古典》之前,刘岳兵就把自己的诗作以油印的方式,编集为《听指集》《单恋集》和《彼此见证》。这些诗作是一个哲学少年的心灵的印迹。诗中,有对人生的思考,有对爱情的渴望,有对未来的憧憬,也有对现实的困惑。但无论处于何种境地,诗人的心境始终是清澈的,是纯洁的,是乐观的。比如《我是山涧里的一尾游鱼》,其中写道:“不用提防一切预谋/所有的雷霆都在闪电之后/不用当心各种暗礁/深渊的表面总有洄水激流”“我是山涧里的一尾游鱼/不问源头不问终了/在透明的清泉中/一样随蓝天和白云悠游”。这是对复杂的社会环境所持的一种人生态度,也是一种我行我素、特立独行的人生选择。
再如,《我愿化作一缕春风》共分三段,均以“我愿化作一缕春风”开头,以“水乳交融”“并肩远征”“连理永终”的誓言表达对于暗恋者的思慕之情。这也不由得使人想起《诗经·柏舟》中的“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这也说明,尽管时代不同,环境各异,但人的感情具有普遍性。只要是真性情,古今中外的心灵都是可以相通的。这也是刘岳兵的少年诗作至今读起来依然能够引起共鸣的原因。
如果说,《飞回古典》是刘岳兵的青春独白,《鱼鸢堂吟草》则是他中年的歌吟,不仅从形式上由自由体变为讲求格律的旧体诗词,更重要的是思想境界的提升。其内容更多的是对友情的赞美,对家乡的留恋,对时事的抒怀,对师长的感念。比如,2020年7月,刘岳兵曾为我们几位同好各治一印,并乘兴作诗,不仅把四人的别号巧妙嵌入其中,而且抒发了大家在一起切磋金石书画的欢快之情。
从17岁负笈马蹄湖畔,到辗转数地回到南开大学工作,刘岳兵在南开园生活了几十年。他对南开园充满了感情,校园中的一草一木都会触发他的诗思。丁香、海棠、蔷薇、碧桐、玉兰、荷花、月季、垂柳都出现在他的笔下,使得这些司空见惯的景物富有了新的生命。他以诗人独特的视角,确定了“南开园八景”,不仅为每一景都刻一方印,而且给每一景都赋一首诗,很是令人赞叹。
刘岳兵奉行尊师之道,在诗中多次表达对老师的感念之请。导师方克立教授去世后,刘岳兵非常难过,他在翻阅《赵之谦印谱》发现“我欲不伤悲不得已”一印时,情不自已,挥泪写下怀念方先生的长诗:“我欲不伤悲,更阑梦影随。梦醒春已尽,舍瑟复何为。弦断声渐远,风姿千古垂。流年嗟逝水,焉可展愁眉,亲炙温而厉,知行永世仪。来昆得垂范,师道自能期。不得已悲泣,镌铭字字痴。师恩何以报,敛泪恐嫌迟。”这些出至真情赤诚的诗句,催人泪下,令人感动。
在大学时代,刘岳兵就开始接触篆刻。铁笔给他带来了无穷的乐趣,而且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使他萌生了出一本印集的志愿。但是,由于忙于学术研究和管理工作,他的篆刻活动曾一度停滞。近年来,刘岳兵重拾铁笔,再续金石情缘,而且成“爆发”之势,他广为搜罗章料,大力购置印谱,又和海内名家广为交流,印艺堪称突飞猛进,日新月异。这也又应了一句话:“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但是,刘岳兵搞篆刻并不仅仅是学术活动和繁忙事务之余的消遣,在篆刻中,他融入了自己的感悟、自己的情怀,篆刻是他抒发情感的一种形式。他自拟的许多印文,都承载着他的喜怒哀乐。比如,2022年春,网上爆出云南省福贡县一位名叫“小花梅”的女士被人贩子拐卖,受尽凌辱,导致精神失常,后经见义勇为者相助,“小花梅”终于得救。有感于此,他刻了一枚5厘米见方的大印,印文是“佛陀还有泪,应渡小花梅”,其悲天悯人之情怀,跃然石上。2024年,刘岳兵刻了一方带有汉印风格的“追蠡精舍”印,表面看起来,似乎只是一方斋号印,但看其所刻边款,才知道其中的掌故:方克立先生25岁时,以“方蠡”为笔名在《哲学研究》发表论文,其父方壮猷老先生特意请金石学家唐醉石刻“方蠡”一印以示鼓励。因此刘岳兵的这方“追蠡精舍”也就有了特定的意义:他是在以此追念导师方克立先生,也是在激励自己以先生为榜样,努力奋发,精进不已。
大学时期,我比刘岳兵高两个年级,因此有过两年的交集。他的《南开日记钞》特别是1985年到1987年部分读起来就倍感亲切,其中的许多事情都共同经历过。多亏了他的完整的记录,使得许多完全遗忘或是模糊了的记忆重新得到了还原。例如,1985年11月28日下午,范曾先生在小礼堂的讲座,我是听众之一。记得那天下午是计算机课,为了听讲座,许多同学都旷课了,从来不点名的老师破例点名,旷课者期末一律给了60分,这也是我大学四年最低的一次分数。通过刘岳兵的日记,范曾先生讲座的情景恍如昨日。因此还可以为刘岳兵的日记作一点补充,就是那天范曾先生讲座的题目是“祖国·艺术·人生”。
1986年冬,范曾先生组织了“东方艺术系列讲座”,其中有一讲我是陪我的书法老师孙伯翔先生一起去的,只记得地点在八一礼堂,具体时间和题目全忘记了。多年以来,我一直想确定一下,但未能如愿。终于,在刘岳兵的日记中找到了答案:这一天是1986年12月26日,讲座的题目是“文学与人学”。
由此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岳兵这本日记的价值会愈加显现出来,正如祝晓风先生在序言中所说:“日记的最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是主人当时的记录,而非时过境迁之后的回忆和追述,因此最原始、最可靠,也就最具史料价值。”“50年后,有人如果研究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史,研究中国大学史、中国青年史,此书就是主要文献之一。”因此,我们要感谢刘岳兵写下了这部日记,也非常感谢他公开这部日记,在一定意义说,它真实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这部日记,是那个时代在一位青年大学生眼中的真实影像。
最后,我想谈一下对刘岳兵个人的印象。我们虽然在大学时期有交集,后来又同在南开工作,但由于专业不同,并没有打过交道,也可以说彼此不相识。直到2018年冬,由于出版《南开日本研究(1919—1945)》的缘故,我们才一见如故,从此就成为很好的朋友。但我们在一起交谈的机会又不是很多,因为他太珍惜时间了,可以说是“惜时如金”,有时他路过我办公室的楼下,或是赠一方印,或是取一本书,他都是放下或拿起就走,绝不坐下来喝茶聊天。甚至在路上迎面遇到,也是点点头、挥挥手,一般不会寒暄。起初,我有些不理解。当看到《三集斋小集》和书后附录的《刘岳兵著述及学界反响要目》之后,我顿时就明白了,正是由于他的勤奋,他的聪慧,他的坚持,他的自律,他的惜时如金,他的废寝忘食,才取得了这样骄人的成绩。这也是刘岳兵的过人之处,值得我们学习。
最后,以一首俚句赠给岳兵教授:“君本衡阳客,卜居沽水边。敏学追蠡舍,勤笃二丘庵。三集传薪火,九樗记流年。金石通大道,墨海著新篇。”